双雪涛《飞行家》:感谢文学,把以往的大雪带回来
- T大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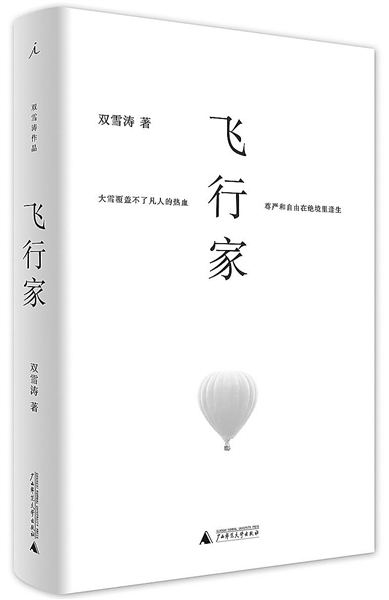
《飞行家》 作者:双雪涛,广西师大出版社2017年8月
读过双雪涛的《平原上的摩西》,我信誓旦旦地跟编辑说,一定会写点评论,结果一直拖到现在。我想,应该是距离太近的缘故。对我来说,双雪涛的小说与朋友在酒桌上讲故事并无二致。东北人都善于唠嗑,讲故事,能把一段很普通的经历,讲得精彩绝伦,但不知从何时起变成吹牛、侃大山了,而且讲的人和听的人,都心知肚明,却共同维持着你爱讲我也爱听的一种和谐状态。其实这特别恶心,也特别不正常。我初步判断,这种变态大概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开始的,在九十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。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,是一个面临下岗的朋友,喷着酒气,说他马上承包某煤矿的某个井,他在矿务局的叔叔已经答应承包给他了,他让我们都跟着他干,不用下井,工资上千,还不包括奖金。这个酒桌上的“煤老板”不久就被迫买断、下岗,真的去了某矿,在矿工上下班的路口摆烟摊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千百万的东北人,差不多都处于这么一种状态。他(我)们知道以前枯燥而稳妥的日子没了,而后是什么样子,并不知道,或者假装知道,用酒,用吹牛或其他方式假装知道。他们以此安慰自己,麻痹自己。双雪涛的小说,一部分在这个背景下发生,另一部分比它早,跟它紧紧挨着,是又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。这种时代,人们裹挟其中,悲欢离合、人性种种,就像漫天大雪,就像日出雪化的街道,显出和往日不一样的景观。
今天说说双雪涛的小说集《飞行家》。其实也就是在说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。不同的故事,相同的内里。双雪涛的小说,呈现了与作者年龄不太相称的沉重感,多是艰难,少有快乐,而且写到了犯罪,死亡,惊心动魄。《平原上的摩西》里,一对两小无猜的小儿女,长大各奔东西,却因为十多年前的几起命案再度相逢,一个怀里揣着手枪,一个包里藏着手枪,相逢在公园人工湖中,惠风和畅水波不兴,读者情绪在他俩的叙旧中一直紧绷着,双雪涛却举重若轻地结束了小说。《飞行家》里的第一部小说《跷跷板》相反,文中已点明了看门人并没死,但“我”居然在跷跷板底下挖出了一具骨骸。
不管乐不乐意,东北人就是比较暴力、直接。而我喜欢的双雪涛小说,全部涉及了犯罪和死亡。孩子间的承诺,竟然引发命案,改变了至少四个人的命运(《平原上的摩西》)。垂死病人的谵语,隐藏了骨骸(《跷跷板》)。皈依宗教的罪人,难逃一死(《光明堂》)。幽会时,情人被害(《北方化为乌有》)。暴力和死亡,因为彰显历史背景而扩大了小说的张力,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欲。但双雪涛的小说绝不止这个。
我们不必深挖小说意义,面对文学,你想挖出来骨骸,就一定不会挖出毛绒玩具。这没意义。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,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。关键是活着时发生了什么。上世纪七、八、九十年代,听着很遥远,其实也就五十年的历史,但街面上已经看不见它们留下的痕迹了。时代快速而疯狂,人们好奇而健忘。双雪涛用冷峻、短促的语言恢复往昔。那个时代,没有高铁,只有绿皮火车;没有上市公司,只有下岗大潮;似乎那个时代的气候,也比现在个性鲜明。《光明堂》里,洗心革面的罪犯,为朋友不惜杀人的德育老师,为忘年交而铤而走险的少年,投靠亲友的小学生……他们都有明确的价值观,并毫不犹豫地捍卫。读者不能轻易判断谁是谁非,只见人性之复杂与幽暗,虽然双雪涛拒绝诗意——他白描现实生活的笔力相当出色——但读者仍可以从“铁幕般的漫天大雪”中感到年久失修老房子里铸铁暖气片透出的些许温暖(那些暖意,瞬间消逝,如安徒生童话的火柴)。为此,双雪涛宁可破坏小说的整体状态,在极其写实的基调里,加入魔幻或超现实主义的段落。这点,小说集《飞行家》比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严重。我还是更喜欢纯粹一些的所谓“现实主义”的小说。
“老赵说,现在的火车真快。柳丁说,是啊,一下就过去了。老赵说,过去我扒过火车,现在不行了,太快了。柳丁说,你说车上的人知道他们刚才经过了艳粉街吗?老赵说,说不准,也许不知道,连个牌子都没有。柳丁说,如果我在车上,我就能知道,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老赵说,那是现在,再过十年,你也看不出来。柳丁没有回答,但是他觉得他能,就算再过二十年,只要是他从窗户往外看一眼,就能知道路过的是不是艳粉街。”
这是《光明堂》中的一段。请原谅我的过度诠释。我觉得这一段正是对人的一生的完美比喻。正如冯唐的垂杨柳,路内的戴城,曹寇的八卦洲,双雪涛将小说设置在一个真实而又恍惚的地方:艳粉街。生于斯长于斯,所以真实;一旦回顾,或者用文字再现,又变得像临终时的记忆,惚兮恍兮,其中有象。我们并不是忘记了“象”,我们只是缺少一个契机。文学,就是复活的契机。双雪涛在不同小说里,让配角儿使用同一个名字(这个伎俩曹寇也常用),而不是主角儿,例如刘一朵。《飞行家》里提到我的老家阜新。这并不奇怪,在双雪涛小说里,你能看到很多确凿的地名。如果你是70、80年代出生的东北人,双雪涛就是在讲你的故事;如果你不是,双雪涛就是在告诉你,有那么一段很长的时间,有那么一大群人,曾经那样活过。 那段日子,就算已经抛离,进入新时代,进入大都市,它也像尾骨、腿毛,在微不足道的地方待着,等待有朝一日重新发现。就像坐车经过艳粉街,一定会认出来。认出来,历史就有了意义,生活就不再荒芜。
《飞行家》里《北方化为乌有》里,“我”是一个进京混饭的作家,一日忽然发现有人写的故事和他的小说一模一样,便邀请这个人来,两个人相互校正记忆,往昔渐渐拼出原貌。
我喜欢的新崛起一代小说家中,粗略地说,葛亮、张草有古意,宁肯有鬼意,路内有暖意,曹寇有痞气,阿乙有静气,不过阿乙有些后劲不足,苗炜和小白有学院气,特别是小白。我并不是不喜欢学院气的小说。学院气也是生活气息之一,只不过离我太远,还是曹寇路内双雪涛他们接地气。双雪涛是冷意,就像东北以前常见的大雪,下雪的时候,如果走在路上,睁不开眼。那种漫天大雪如今罕见。感谢雪涛,把以往的大雪带回来。



















